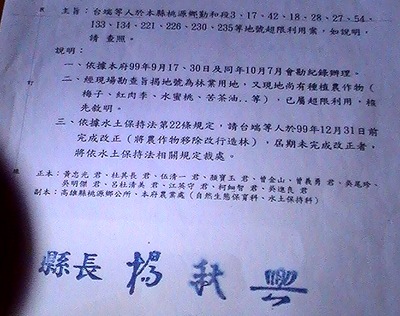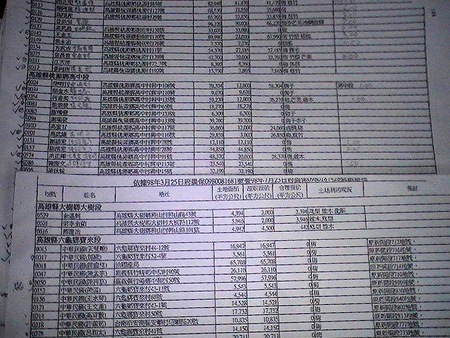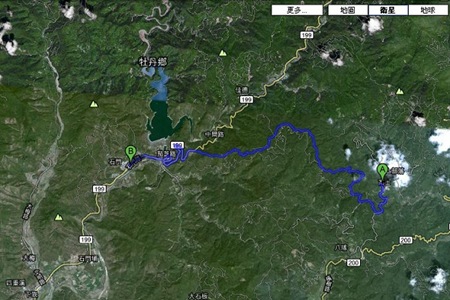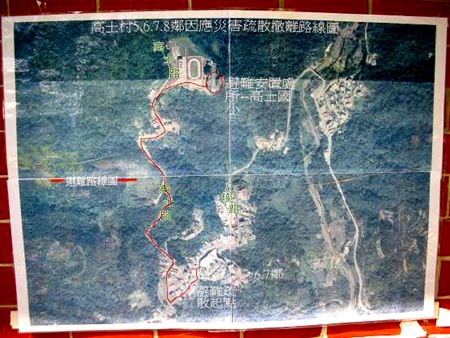編按:11月12、13日在台灣師範大學舉辦「一年過後:原住民族災後重建與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圓桌論壇以及議題發表討論的方式進行災區的族群代表、NGO代表、政府代表之間的對話。本文為會議整理系列報導(3),閱讀系列其他文章,請見文末附錄。前言:
災後重建在國家角色消失的狀態之下,慈善團體所建立的「生活重建中心」只能解決個人的問題,而這個生活重建中唯一沒有被重建的就是部落。所以看到這樣的一個過程,社會福利組織必須要重新的回到尊重原住民自治的一個原則裡面來自我自治跟約束。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王增勇表示,「進去到原鄉組織只是陪伴的角色而不是一個發展的重點,換句話說災後的重建並不是社會福利來擴大版圖的一個過程,而應該是回來問在這個過程裡面到底有沒有讓在地的部落更有力量。」
但他也表示,在那個過程裡面,社會福利組織必須非常自覺得進行組織型態的調整,但讓在地力量出來是社會福利組織最容易迷失的地方。因為在那個裡面大家很可能進去只為了搶資源只為了發展自己組織的更多組織。而卻忘了說讓部落有更多的參與。
「生活重建」幫助了誰?是增強災後部落族人自我復原的能力,還是壯大社會福利組織的架構?以下是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王增勇觀察災後重建現象的相關整理報導。

王增勇表示,災後的重建並不應該是社會福利來擴大版圖的一個過程。
一、災後重建的福利問題與現象
(1)「福利殖民」現象
王增勇表示,從災後重建以及社會福利的角度來看,不是只是針對重建而是八八風災的重建的現象去理解。從原漢的一個角度來看,社會福利已經成為外來福利機構一種介入部落生活方式的一種殖民現象。並且他也表示,姑且把這個現象稱為「福利殖民」。
他也表示,透過經濟型態的改變與介入,社會福利變成文化殖民上的一種殖民的型態。而這種文化殖民的形態其實它的改變是更深層,因為它改變的是原住民對於自我認同的問題產生。
所以這樣的福利行為,表面上它是一種助人的行為,但是實際上更深層改變的是原住民的價值觀跟信仰,而且更否定的是原住民過去這幾千年延續下來的集體族群的認同。
(2)「八百壯士」與「福利街」
他也更進一步說到,從九二一的就業大軍到現在的八八臨工,可以發現原住民部落現在進入的這些社會福利經過這一連串災難打造出來的一個現象就是現在在部落裡面可以看到的所謂的「八百壯士」。
王增勇從過去的觀察表示,這個助人的歷史其實也不是只有在九二一之後才慢慢的發生,從基督宗教進入到原鄉,用麵粉搭配著福音傳教來助人,進行了信仰上面根本的改變。
而90年代之後,有了原民會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福利方案開始進行,進入原鄉去推動。其實這樣的一個過程其實都根本的去改變原住民傳統的一種對於勞動的看法,而讓八八零工改變了原住民對於工作對價關係後面的價值觀。
除了各式各樣的生活重建中心成立,從這次莫拉克風災政府開始委託各個民間團體進入各個受災鄉鎮成立生活重建中心。形成災後整條街都是外來各個團體所成立的生活重建單位,而演變成部落裡有所謂的「福利街」的現象。
他也表示,這些社會福利的進駐其實背後都是有一個共同的邏輯,第一點就是把集體的社會問題變成個人的問題來解決,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部落消失了。
二、生活重建中,唯一沒有被重建的就是「部落」。
所以王增勇也表示,「在這種強調個人,國家角色消失的狀態之下,慈善團體所建立的生活重建中心只能解決個人的問題,而這個生活重建中唯一沒有被重建的就是部落。」
那個集體性部落在這個裡面是消失的,從「永久屋」的例子來看,部落在這個裡面是被拆解的,甚至於是因為資源的介入,分配的不均而讓部落產生更大的衝突。
原來有的一些在地組織在這個重建裡面,反而都被瓦解。所以換句話說重建並沒有把部落當成是一個要重建的一個對象。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大愛屋」並不是一個個案,它是延續過去四百年原住民在跟漢人之間這個關係的不斷重複出現的一個現象。
在這個現象裡面原住民主體性的消失,原住民永遠成為一個受助者,然後只能夠接受外來的專業人員以及外來社會福利組織的重建方法。
三、在「福利殖民」的運作方式下,原住民的文化無法延續跟傳承。
他也提醒到,現在大量的社會福利組織進入到原鄉從事重建的時候,部落是要小心這些狀況。
他表示,「事實上在原鄉重建裡面大家會不斷的看到生活重建中心的工作人員,只要有人潮聚集的地方,就會去照相。大家不斷的在搶人,不再問說所辦的活動到底對部落有沒有幫助。」
因為社會福利組織要負責的是給錢的單位,給政府單位,給評鑑的學者。但是社會福利組織唯一不負責的就是他所服務的部落。所以是這個關係要根本的被改變,不然的話那個重建到底是在重建誰?重建什麼?

在原鄉重建裡面大家會不斷的看到生活重建中心的工作人員,只要有人潮聚集的地方,就會去照相。大家不斷的在搶人,不再問說所辦的活動到底對部落有沒有幫助。
部落自主重建的權利?!
王增勇表示,國家在災後「生活重建」的過程裡面極小化政府應當承擔的角色,委託給民間團體辦理,而無形中讓民間團體之間產生一種競爭的關係。
因此政府可以選擇聽話的民間團體來進行辦理,所以這些民間團體接受了政府的委託,其實它能夠掌握的自主性是相對的少。所以國家可以在這裡面,又進行操控但是又隱身在這些團體的後面。
「生活重建」政策讓政府隱身在慈善機構的背後操控,而當部落重建的問題不斷發生的同時,部落災民的權利又在哪裡?

王增勇表示,慈濟大愛村反應的是助人者的世界觀,而不是受助者的觀點,這種文化殖民代表著長久以來原漢關係中漢人中心的思維,表面是一種助人善行的表現,背後實則代表對劣勢族群文化點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