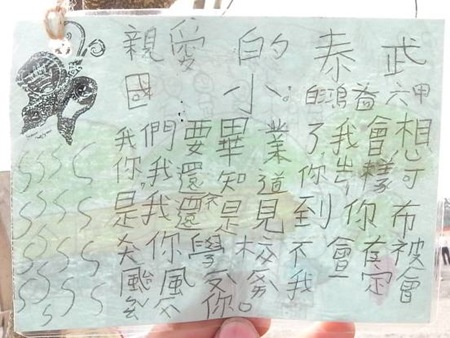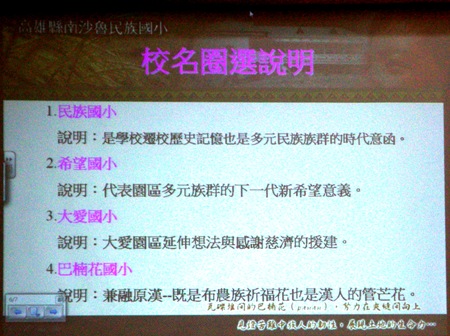「你們是來這裡做什麼的?國稅局派來調查的嗎?」居民在政府進行災後重建過程中,產生對外來者的不信任和抗拒,這也同時是普遍藝術進駐社區計畫共同要面對的問題。

小林社區的十二生肖雕刻創作。
猶記得2009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造成滅村、走山、土石流、人民流離失所,至今已過了一年多了。政府與相關機關急就章的重建政策,腳步依然緩慢,也因此在2010年8月6日的凱道上重新燃起狼煙,齊聲抗議政府的重建不力。
事實上,協助災區重建的經費從沒有少過,但卻是透過公部門釋放出計畫案,再經由民間財團/公司/社團競標申請,通過之後才進入災區或安置所內進行各項重建工作。而這也出現各項計畫案之間沒有整體性的規畫與整合,無法有最實質上的幫助。
這並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卡催娜颶風之後的美國紐奧良、南亞海嘯之後的斯里蘭卡、大地震過後的智利馬烏萊大區…,這些地方都經歷了重大災難後的「震撼治療」。
這樣的震撼又被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天災/災難本身所造成的震撼;第二是以快速推動重建與以經濟成長之名,將重建工作外包給財團,造成國家失去應有的能力,並將執政的責任透過有系統的方式委外辦理;第三是人民因此得到過多的犧牲,離開家鄉、釋出土地、文化與生活方式產生斷裂,重建經費落入各大財團/公司/社團的手中,經過層層轉包各自拿到應有的利潤之後,實際給予當地雇工的經費少之又少,最後整個重建過程造成「受害者再度受害,遭到剝削的人繼續被剝削」。
大多數人將這樣的過程視為理所當然,許多NGO組織也不自覺的以參與進行的方式被整合進新自由主義化的計畫中,形成社會參與的表象。
在這樣的災難背景下,旗美社區大學眾多學區遭到嚴重破壞,各鄉鎮面對淹水、農損、安置、遷村等重建生活的課題,更挑戰社大經營與設計課程的彈性,也開始思考著學習作為一種重建的方式。
因此2010年3月首次嘗試將藝術帶入88風災的災區,其分別為小林社區、荖濃社區、甲仙社區。邀請3組藝術家:甲仙/孫華瑛、小林/林純用、荖濃/陳正一、歐陽慧英、林雨君於4月份開始進駐,至7月份結束駐村。這次計畫主題為「重建生活‧藝術行動」,希望能從多元的角度,帶給3個社區不同的藝術體驗,希望經由藝術家的長期陪伴,讓災區居民重拾過往的信心與歡樂,更能由此逐步建立社區自主性,凝聚共識,經由共同的成長與創作、藝術性的對話,讓社區組織發展與生活美學產生不一樣的視野。
「重建生活‧藝術行動」
這是個由民間組織自行發起的藝術計畫,行動在2010年3月份悄悄的開始進行。策展人孫華瑛與旗美社大工作人員走訪數個受風災影響的幾個社區,了解各項重建、救援的狀態與在地組織和居民的想法,試圖先了解在地的需求與藝術家是否適合在這時間進場。透過不斷的討論與了解社區需求後,再決定駐村地點,並且以小規模、不喧嘩的方式透過藝術團隊的陪伴來看見社會性的觀點。
這是一個軟性的、無形的藝術陪伴與創造過程。藝術家孫華瑛、陳正一、歐陽慧英、林雨君等人同時身兼藝術工作者、社工人員、劇場工作者的角色,以心靈陪伴與組織社區再造做為藝術駐村的目的,來開啟居民開放式對話的空間,產生彼此的信任關係與學習傾聽和同理心的建立。藝術家林純用則是希望透過視覺與社區帶動的方式,讓除了視覺上裝飾美化的功能之外,還希望能讓居民重新找回自身傳統技藝,透過這樣的方式讓居民對藝術家駐村防衛心降低並產生信任關係。
「你們是來這裡做什麼的?國稅局派來調查的嗎?」這是藝術家初到社區時民眾最直接給予的回應。居民在災後政府重建的過程中,產生對外來者的不信任和抗拒。但這樣的回應也同時是普遍現今藝術進駐社區計畫中共同要面對的問題,藝術家進到社區3個月創作完畢離開後,留下了什麼?一件在成果展過後就塵封起來的攝影/裝置作品?一件看不太懂的雕塑/繪畫?一場只需表演一次的社區劇場?在災難過後,居民為了重建家園、為了家庭生計,怎麼還會有多餘時間去理會這些拿了重建經費的外來藝術家呢?
藝術進駐在此時不該只是做些藝術創作、藝術活動,似乎也要敏感到在地生態裡社區工作的權力關係。因為當藝術家離開後,社區的主軸仍然是這些生活在當地的居民,她們的自主性應該要被引發出來。而進入的姿態、切入的角度都是藝術家與社區居民可以一起創造出來的。透過不一樣的媒介(有形或無形的)來擾動居民,並以社區的環境、生態、組織等公共議題來進入社區生活。這樣的過程使得藝術駐村不一定是去解決問題、創造新的事物,更重要的是在於發現自己和彼此(社會)關係的過程。
婦女在社區中的集體實踐
「用婦女的力量帶起社區的運作」這是策展人在藝術計畫中最重要的目標之一。「重建生活‧藝術行動」中參與最多的是社區中的婦女,男性大多需在外工作,而女性則負擔起傳統照顧家庭的角色。在災後,柔腸寸斷的聯外道路、紛擾混亂的重建角力,讓居住在內的居民無暇再去思考到日常生活之外的事件。因此地方組織四分五裂(小林社區),居民對於生活大多採取認命與無奈的態度。能夠讓彼此產生關聯的公共議題僅有在共同的信仰與祭典上。
在某些女性主義式的觀念中會認為女性與自然有著某種特殊的關聯性。像是比較能夠關心環境破壞的問題、比較能夠照顧孩子、與自然有較多的接觸,最後延伸成為與大地之母的和諧一致,一種近似於女性崇拜的想法。而在這次的藝術計畫中,則是將女性的力量放置在「發揮與讚揚我們自己的人性魅力,而非尋求未知的療癒」上。所以在荖濃駐村的藝術家透過劇場式的肢體表達練習,重新喚醒這些婦女本來就很珍貴的知識,像是平埔族的文化、耕作的記憶等這些平常不以為意的生活方式,產生對自我價值的提升。

荖濃社區的駐村藝術家:歐陽慧英(左)、陳正一(右)
甲仙駐村藝術家孫華瑛也是透過社區劇場的形式,讓參與的婦女引發更多對話。在甲仙鄉除了「甲仙愛鄉協會」的地方組織之外,還有許多新移民姊妹。這些新移民姊妹是為了脫離當地的貧窮,期望可以透過婚姻來讓命運翻轉,所以在災難過後這些每個人都是穩定社會的因子之一。
「我不希望別人以為外籍的都只能做勞力,其實還可以做其他的工作」,這是新移民姊妹-美玉在成為重建人力工作者之後所給予自己的期許。在社區劇場課程中,藝術家嘗試帶出對於「社區服務據點」的想像和期待,並且由婦女們練習統籌相關事務,練習彼此的互助學習精神,更多豐厚的力量也隨之蔓延。

甲仙愛鄉協會的伙伴們。
共有的習慣在社區中,正悄悄的修復重建中。E.P.湯普森在《共有的習慣》中指出十八世紀英國工人農民社區中所強調的「習慣」,其實並非我們所談的一成不變的「傳統」,而是平民百姓為保障自身權利的辯解、慣例以至地方的律法,有些甚至是一些「晚近的創造」。
在荖濃的廟會祭典儀式是一般常見的傳統,體現了族群多樣的社區型態,包括平埔族、原住民、客家、閩南等族群的融合;地方婦女參與組織行動使得實質上促進民眾行動自由和基本權利,使她們不完全受統治者的宰割和支配。組織進行的方式產生更有豐富的多元面向,而這經常會以情感豐富的公共儀式和反抗表演的形式出現。
災難過後,藝術家進駐社區的難題與省思
此次藝術進駐計畫中受到最艱難阻力的是在小林社區。在這裡住在大愛村的災民面對「震撼治療」後的重建腳步,社區組織四分五裂,使得受害者仍持續受到災難,而駐村藝術家林純用更曾經打算收拾行李,一去不復返。這過程中支撐藝術家背後的動力來源在哪裡呢?或者換個問法,藝術家為何明知此次計畫路途遙遠、困難重重,仍願意繼續待在社區中陪伴居民的成長與互動?
持續性(時間性)的問題,對於新類型公共藝術來說是最為嚴苛的。因為這表示在一定時間內需完成的藝術裝置,可在可掌握的展覽空間中被展示,且將耗盡所有背後的支持系統。在新類型公共藝術中,會將藝術當作公民論述或公眾教育,或者視為社區組織和政治行動的想法。
這類有形的或無形的藝術創作常會和社區工作者混淆,或是難以被認定為創作類型,藝術家也常需要面對很大的風險,在與社區完全合作的創作方式,很可能駐村成果是與不漂亮的東西連結,因為過往的美感經驗必須被適度的排除。這會使得傳統學院出身的藝術家產生對創作的懷疑,如在此次藝術駐村期間有位大陸藝術家的到訪,提出的疑惑是:「為什麼藝術創作要面對如此複雜的社會問題?」。策展人孫華瑛巧妙的回應道:「這是一場藝術參與社會的行動」。
官方辦理的藝術家進駐社區計畫,常會因為招標與考核制度而使得過程複雜化或僵硬化。因為公部門辦理的計畫無法接受未完成的、失敗的或無形的成果。因此藝術家和行政管理者之間會形成密切合作的關係與機制,目地是在結案時能有一項具體可看見的物件產出。而此次由民間組織-旗美社區大學自行籌畫的藝術家進駐計畫,恰好可迴避公部門所需面對的難題。此次參與計畫的工作人員與藝術家以這樣的基礎發展出另類的文化(藝術)行動,雖彼此磨合機制尚未成熟,但未來持續經驗累積也將產生更大的可能性與多元文化交流的機會。
參與藝術進駐計畫的藝術家們對於為何能夠堅定的陪伴災區的社區居民到駐村結束,也無法有具體的原因來描述,大多只能苦笑著回答我們僅是從事藝術行為的傻子,憑著一股熱情和擊不倒的意志力來完成自己的許諾,陪伴著居民的成長也面對自己的成長。
但是光憑靠「熱忱」所支撐的行動,為何非藝術家不可?或者為何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士不被談論?台北藝術大學教授吳慎慎有個另類的解讀──
「在當代的生活中,不管是不是藝術領域或其他領域的人,每個人生活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找到自己生存的意義,此次藝術進駐計畫參與的老師和工作人員搭起一個很好的空間,能讓大家在裡頭相互找尋彼此,找到彼此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它的價值是來自於這是最貼近真實生命東西。這種真實性和能量會不斷的發散和發酵,不會改變。我們在彼此身上辯證了彼此的存在與意義。……這種這麼偉大的事難道真非你不可嗎?只要有人有一個熱忱的心,願意嘗試各種方式跟居民溝通,那為什麼一定要是藝術家?這真是藝術家自己該去檢討的問題,做為一個藝術家連自己跟別人不同的地方在哪裡都不知道。
如果我們認為一個醫生他本身具有很多藝術的素養、方法、具有同理心、可以跟別人對話、具有願意和別人連結的習慣,若這樣的人進入社區,那必定是不會比我們差的。換句話說若換成另外個藝術家,他其實沒有這些特質,他的同理心、他的對話能力,他所做的藝術其實並不會跟別人產生關係,如先前提到的大陸藝術家,這些人很對都沒有錯,大多數人不想面對複雜的社會問題都是一樣的原因。……但是所以說為什麼非藝術家不可,可換個方式說『我們需要的是具備有藝術資質的人,有上述能力的人』來參與,無關乎身分、職業和專長。」
從這些對話與提問中不斷的辯證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這或許不會帶給大家對於藝術進入社區所面對問題的答案,但每個人都可以從各自的實踐中找到自己對於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或許這就已足夠。而這些理論或經驗的發展,仍需要更多人的參與才能創造出更多元的發展。
可參閱,劉美妤,「一年後,他們在凱道上燃起狼煙-淺談八八風災重建之弊」,《破周報》第623期,2010.08。
可參閱,李孟霖,「不只創意,原鄉文創「行銷」待突破」,莫拉克新聞網,2010.11.12。
可參閱,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2009。
可參閱,孫華瑛,「甲仙鄉藝術家駐村筆記:教室在窗外」,旗美社區大學,2010.05.22。
可參閱,孫華瑛,「甲仙藝術家駐村筆記:災後重建工作者-新移民姊妹-美玉」,旗美社區大學,2010.06.03
可參閱,E.P.湯普森,《共有的習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09。
可參閱,許寶強,「重讀湯普森.認真多角度」,《通識plus》試刊號,第二期,2010。
可參閱,Suzanne Lacy,《量繪形貌-新類型公共藝術》,吳瑪悧等譯,遠流,2004.11。
(本文轉載自2004-2010年行政院新聞局製作之「小地方-台灣社區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