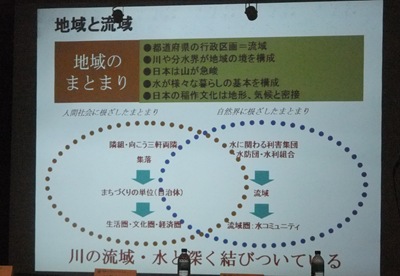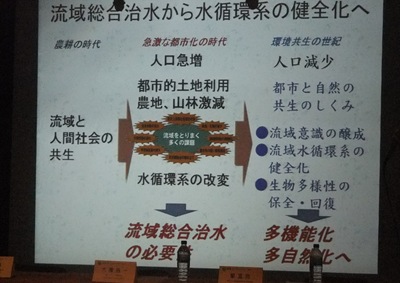雖然在大部分台灣人的眼中,河流仍不過是水道,但少數民間團體卻早已體認河流生命系統的重要性,竭盡所能保護台灣的河川。如果,我們能夠將河流視為一個生命系統,好好呵護她,河流也會持續不斷地我們提供免費的午餐…
如果說天下有白吃的午餐,那麼河流就是這白吃的午餐,一直以來提供人類許多免費的服務。
過去,河流為人類帶來了水源、食物、農作養分、航運之便等好處,孕育了人類的古文明,被視是母親般的生命體。今天,當許多城市裡的人們已不需再依賴都市河流的漁獲、也不用就近取水時,看待河流的態度也不一樣了。
一條被遺忘的河流,一道消失的水域
在都市開發的過程中,許多沒有航運之利的小河在人們眼中愈來愈無用,似乎唯一的功能就只剩下排水與排汙了。
兩年前我走訪了泉州的后墩村,從地圖上看,這村子有條蜿蜒小河流經,但現實並非「我家門前有小河」那樣美好,這條小河奇臭無比,而且因為承載太多垃圾,根本流不動了,從水域變成陸域,魚兒不見了不說,還有許多老鼠竄來竄去。
河流已死,后墩村的人們仍在死去發臭的水體旁居住、吃飯、工作。


死去的泉州的后墩村的河流
泉州,是中國近年來經濟迅速發展的區域之一,工廠和道路開發的速度之快,讓任何一張新出版的地圖馬上就過時;也因此吸引了中國內地鄉下的人們蜂擁而來,擠進了成千上萬像后墩這樣的城郊村落,在許多地方,客居異鄉的外來勞工甚至多於本地居民。
沒有地方認同感,又為了討口飯吃,人們選擇對環境汙染和健康威脅視而不見。
另一方面,他們也沒有其他選擇,因為后墩 不過是數不清類似社區的縮影,許多可以提供工作機會的發展中區域都面臨著嚴重的環境汙染問題。
在那個炎熱的仲夏,我連續幾天得前去后墩進行調查。每天,高溫加上惡臭讓我待不到幾小時就頭暈目眩,但這兒的人顯然處在鮑魚之肆太久,不聞其臭了。
我問村中的居民,這條流經村落的小河叫什麼名字,村民說:「那有什麼名字,就是條排水溝嘛!」
當河流只是條排水溝,甚至連名字也被遺忘,最後的命運就是被摧殘至死。
被當成排水溝的都市河流或許還算是「好命」的,有些在精華開發地段的河流甚至被認為是「占用」空間,乾脆填埋起來,從人間蒸發。有些河流雖然仍在地下的水泥管道中流動,但人們眼睛看不到,自然也不會想起;這些地下河流對人們來說等於消失了,而河流中的生命自然也一併逝去。
在台北,過去的灌溉渠道被填平、被地下化了不說,許多自然小河再也不見蹤影。在太平洋另一端的西雅圖,即使以山水環繞的景致著名,但城市中找不到幾條河流,不是因為這裡沒有河流,而是在都市發展的過程中被徹底驅逐了。
被遺忘的地下河,翻身重見天日
與開發中國家的河流普遍遭到嚴重汙染比起來,先進國家的河流即使也曾有過類似的身世,但現在幸運多了,當工業廢水和家庭已不再直接排放到河流中,不少河流已在復健中,漸漸恢復了生命力。
河水乾淨了,人們也開始發現河流的美好,慢慢找回對河流的情感,於是有些被埋在地下的河流,也得以重見天日(’daylighting’)。
在美國就已有不計其數的案例。舊金山灣區(San Francisco Bay Area)可以說是最積極讓溪流重見天日的地區了。早在一九八四年,柏克萊(Berkeley)就乘打造新公園之便,打開了原本被埋在基地下的草莓溪(Strawberry Creek)。此外,歐洲的丹麥、英國、瑞士、德國等地,也都有類似的案子。
在亞洲,韓國的清溪川則是台灣人耳熟能詳的例子。二十世紀中葉,在經濟發展重於一切的社會氛圍中,流經首爾的清溪川被覆蓋起來,隨後更在上方築了一條高架橋。
可喜的是,這樣的窘境在本世紀初有了轉機,為了改善都市的形象,首爾市政府拆了高架橋,移去了覆蓋在清溪川上的水泥,並為水岸做美化、綠化。
現在的清溪川已經一躍成為首爾最受歡迎的公共空間和觀光景點之一了。但令人遺憾的是,讓清溪川重見天日的考量僅著重於塑造親水景觀,而不在復育河流生態。
被折騰數十載的清溪川其實早已乾涸,現在則得仰賴人工幫浦從漢江引水來重現水流,耗資巨大。
今天的清溪川不過是一條假的河流,並未重生、也沒有生命力!
清溪川的例子固然令人失望,但愈來愈多城市願意打開被覆蓋的河流、重塑與河流的關係,仍是令人欣慰的趨勢。
城市與水相融,水都的和諧表象
當都市河川和其他水體不再積滿垃圾、不再發出惡臭、水鳥願意造訪,甚至還可以看到魚兒的蹤影時,水也成了賞心悅目的城市風景。
許多富裕地區的城市開始打造親水環境,人們也愈來愈喜歡住在水邊,水岸住宅因此大受歡迎,成為炙手可熱的房地產。今天,有著交錯縱橫水道的城市也分外迷人,例如威尼斯、阿姆斯特丹、斯德哥爾摩等歐洲著名的水都。
然而,改善了水汙染問題、製造了親近河流的機會,就代表河流不再受人類折騰了嗎?看似乾淨的河水,代表河流回復生態系統的健康了嗎?
可惜,答案是否定的。
城市與水融為一體、和諧相處的水都表象,其實不過是人類高度控制的結果,荷蘭,就是最好的例子。
荷蘭位在歐洲大河萊茵河與繆塞河(Meuse)出海口,原本是一個生態豐富、密布著河道、湖泊、濕地的超大型三角洲;世世代代的荷蘭人為了農耕和開發聚落,不斷「重新整理」地景:抽乾了濕地的水、以硬體工程限制河川的變動、開鑿運河與渠道以利航運與灌溉。
今天,許多荷蘭城市有著密密麻麻的運河穿梭其間,是航運與休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造就了荷蘭獨特的水都風情,令台北人羨慕不已;反觀流經台北的河流,總被阻絕於防洪牆或堤防之外,看不到又難以親近。
荷蘭之所以能夠有易於親近的都市水環境,是因為他們高度控管運河水位,就算河流氾濫也不會受到影響。
對水文環境的高度控制,當然也就箝制了河流自然律動所創造的生命力和生態多樣性。




荷蘭阿姆斯特丹與烏特勒支的河流與城市。
荷蘭城市中的水道雖不再是排汙的管道,但也只剩下替人類服務、提供視覺和經濟發展的功能而已。人們看待河流的態度在本質上沒有什麼重大的改變。
換句話說,無論是水與城市融為一體的阿姆斯特丹、築起高堤阻絕都市與河流的台北、視河流只是條排水溝的泉州后墩村,人們都不在乎河流本身的生命力。
在歐美地區,當水汙染問題得到控制之後, 河水變清澈了,專家學者卻繼而發現人類對河流的高度控管仍然持續傷害著河流生態,而且程度絕不小於河川汙染。
為了航運及防洪,人類利用各種河川工程來改造自然河道並對水流進行控制,例如截彎取直、河道水泥化或是打上版樁、築堤防、建水壩和攔河堰等。
只要人類對這些控制不做任何妥協,那麼河流永遠不可能回復健康。
河流不只是水道,也是生命
許多人可能會想:那些被嚴重汙染、徹底改造的都市河流反正已經沒救了,還不如把財力和精力花在保護那些荒野中,或是國家公園裡的河流。但事實上,讓都市河流恢復健康的重要性不會小於保護那些尚未遭到重大破壞的河流。
許多都市位在大河的下游,因為水往下流,讓人們以為下游發生的事情不會對上游產生影響,但其實不然。
世界上許多河流孕育著洄游性的魚類,例如鮭魚,洄游性的魚兒在河川中、上游出生,在大海中度過大半生後,會再度回到出生地孵育下一代。
不管是小魚從河流游向大海,或是成魚從大海回歸河流故鄉,都得通過下游城市這一個關卡。若城市河流汙染嚴重、沒有適當的棲息環境,又加上水流的擾亂,不但嚴重威脅了河海物種的繁衍,也連帶影響海洋和河川上游生物鏈的平衡。
近幾十年來,西雅圖慢慢瞭解都市河流對鮭魚保育的重要性,花了許多心力來改善都市的河流環境。
西雅圖人知道河流除了為城市提供經濟、休閒和視覺功能外,還是一個生態系統;他們所看到的河流不只是水道,也是生命。

西雅圖的都市河流對鮭魚保育十分重視。
然而,修復都市河流的工作困難重重。除了既有環境的牽制和復育計畫的預算限制,相關工作只能著力於治標而無法治本,因此美國西北地區的學者普遍認為,都市河流復育的效益僅在於提供環境教育的材料,對於改善實質生態功能的幫助並不大。
不過,柏林的研究團隊卻有不同看法,認為即使是再微不足道的改善工作,也可能改善河流生態,於是,他們採取了實際的行動。
由於柏林的幾條河道是城市中不可或缺的航運管道,目前無法進行大規模生態復育的改善工作;但為了減低航運對魚類產生的負面影響,柏林研究人員選擇了兩處船隻往來頻繁的河段,在靠近河岸的水道中加了道「保護牆」,當船隻往來激起洶湧波浪時,保護牆與河岸間的區域可以成為幼魚的避風港。這是個實驗性的計畫,希望透過這樣的小動作來增加幼魚的存活率,進而維護都市河川中魚類的繁衍。


德國柏林河道的護魚牆生態復育
目前研究人員正針對保育的效果進行監測調查,但不論效果如何,就是要有這種永不放棄的信念,都市河流才有回春的希望。
台灣人又是如何看待都市河流呢?
對大部分台灣民眾來說,河流是帶來水患的麻煩製造者,無不希望政府快快築堤、疏浚整治;但另一方面,民眾卻也愈來愈希望能夠擁有親水的機會。
雖然在大部分台灣人的眼中,河流仍不過是水道,但少數民間團體卻早已體認河流生命系統的重要性,竭盡所能保護台灣的河川。不幸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卻仍固守落後的思維,總是視河流為不聽話的水道,或是沒有好好利用的空間,動不動就要水泥化整治,或興建沿河快速道路,正因為他們看不到河流的生命。
如果,我們能夠將河流視為一個生命系統,好好呵護她,河流也會持續不斷地我們提供免費的午餐;而那也會是一個都市與河流河流和諧相處的新世紀。
(作者為美國華盛頓大學博士候選人,地景及都市設計師,本文轉載自「好城市,怎樣都要住下來」一書,野人出版)